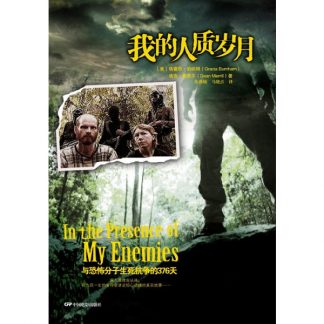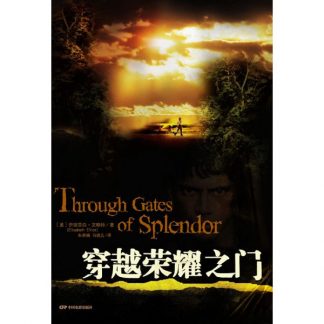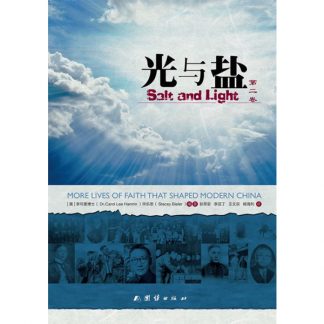描述
| 报佳音号 | 6625 |
|---|---|
| 外文书名 | Salt and Light, Volume 2: More Lives of Faith That Shaped Modern China |
| 品牌 | ZDL |
| 作者 | [美]李可柔博士、毕乐思 编 |
| 译者 | 彭萃安、李亚丁、王文宗、杨海利 |
| ISBN | 978-7-5126-3208-0 |
| 出版社 | 团结出版社 |
| 出版年月 | 2014年12月 |
| 开本 | 16K |
| 页数 | 321页;240千字 |
《光与盐》(第二卷)推荐辞
这本书说的是历史,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讲的是以往的志士仁人,却有益于今日的平民百姓。所以我很希望,有幸能够识字读书的年轻“读者”,不但要读读这本书,更要深长思之,并且起而行之!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基督教经典译丛”主编、《大家西学:信仰二十讲》编者
《光与盐》(第二卷)主题
探索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名人,影响近现代中国的信仰人生。
《光与盐》(第二卷)内容简介
本书中介绍的这些人物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之际,致力于维护中国社会,坚忍地回应时代挑战。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所服务的机构,为重建中国社会以促进战后中国复兴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贡献。本书介绍的这些人士不仅以他们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更以他们的人格品德祝福了他人。我们希望,他们的事迹能够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和激励。
本书属于“光与盐”系列丛书,同属此丛书的还有《光与盐》(第一卷)、《穿越荣耀之门》、《奥卡人的新生》、《巴西丛林笔记》和《梯田上的咖啡》等书。
《光与盐》(第二卷)作者简介
李可柔博士(Carol Lee Hamrin),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教授和世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这两个机构都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她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中文和比较世界史博士,之后任美国国务院研究专家二十五年。2003年,李博士因其杰出的公务活动获得公共正义中心的“领导奖”。她在华盛顿地区的几所学院教授研究生课程,并有若干书籍和文章面世。她的著作包括《光与盐》(Salt & Light,2009、2010和2011版)、《上帝和凯撒在中国:政教张力的政策含义》、《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决策过程》和《中国与未来的挑战》等书。
毕乐思(Stacey Bieler),《“爱国者”还是“卖国者”?——中国留美学生史》的作者。作为《光与盐》(Salt & Light,2009、2010和2011版)的合编者,她撰写了关于容闳、梅贻琦、晏阳初以及徐氏家族的数篇文章。毕女士1994年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作为独立学者,她与人合著了《中国就在你门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和福音》两本书。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国际节目社区志愿者董事会担任董事。
除本书外,两人还共同合编了《光与盐》(第一卷),介绍了晏阳初、林巧稚、石美玉和梅贻琦等对中国现当代史影响至深的基督徒。
谁适合读《光与盐》(第二卷)?
- 渴望以圣经为原则、以神为中心来生活的人
- 渴望从“历史角度”了解基督教信仰带来影响的人
- 渴望拥有光与盐的人生的人
- 渴望深入了解真实历史的人
- 渴望反思生活和希望自己的生活作出改变的人
- 渴望牧养教会的人
- 渴望学识和学术以及历史知识上有所提高的人
- 渴望传递真理给别人的人
《光与盐》(第二卷)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 拥有真理的信仰可以活出光与盐的人生;
- 信仰人生带来历史的改革;
- 美好的品格和真实的信仰激励后人前行。
《光与盐》(第二卷)目录
导论:光与盐人生
- 第一章 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颜永京、颜惠庆父子
颜永京是最早从美国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国人之一,曾协助创立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儿子颜惠庆在动荡的民国初期先后担任过总理和外交部长。
- 第二章 教育改革先驱——马相伯
马相伯出身于一个杰出且具影响力的天主教家庭,是复旦公学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并参与中国科学院的创立。
- 第三章 胸怀愿景的革命家——黄乃裳
黄乃裳在辛亥革命前,一直是中华民国创立者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支持者,清末创办在沙捞越(现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属地,后来成为记者,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领袖,民国初期福建很有影响的政治家。
- 第四章 从苦力到教育家和慈善家——邝富灼
邝富灼出身贫苦,凭个人奋斗在国外获取高等教育学历。作为商务印书馆英文主编,他影响了几代中国的英文读者。他亦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扶轮社的奠基人之一。
- 第五章 黑暗中的光——尹任先
尹任先协助开创了中国纺织业,作为民国时期的高级财经官员,其廉洁闻名遐迩。二战后,他在苏州创办了圣光学校。
- 第六章 秉持基督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教育家——曾宝荪
曾宝荪留学英国,回国后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该校是首批由中国人主办的女子中学之一。她的远见卓识与交际能力,连同她显赫的家世,使其影响力遍及国内外。
- 第七章 牧者与学者——刘廷芳
刘廷芳是燕京大学颇具影响力的教授,也是中国基督教杰出的教会领袖,曾经主编一份重要的基督教刊物,力图改革民国时期的教会和社会。
- 第八章 一生为大地耕耘者服务——张福良
张福良获得林业学和农业学硕士学位后,带领基督教会从事农村重建工作,二战期间领导救助中心工作,帮助成千上万难民逃往内地。后期在美国生活,面向世界各地推广先进的扶贫方法。
- 第九章 法官、天路客和诗人——吴经熊
吴经熊成人后皈信天主教,是著名的国际法律学者和法官,曾协助起草民国宪法,亦曾作为中国代表出使梵蒂冈。他翻译的《诗篇》和《新约》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 第十章 电影教育的先驱——孙明经和吕锦瑷
孙明经、吕锦瑷夫妇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教授电影制作与摄影。孙明经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吕锦瑷制造出中国第一批感光胶片。金陵大学电影部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
- 第十一章促进愿景的中国当代女性——王立明
王立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社会活动家之一,领导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会长达三十年之久,并成功地为妇女争得选举权。她和身为大学校长的丈夫刘湛恩共养育三个孩子。
本书人物大事年表
作者简介
注释
封面及正文图片资料来源
《光与盐》(第二卷)书摘
愿景实现:震旦学院
为了表示这所新型学院首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马相伯命名它为“震旦学院”。古文“震”字常用以指东方;而“旦”字则表示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在马相伯看来,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国光明前景的开始,犹如东方的晨光,预告着新一个黎明的到来。为了体现这所学院是中西方教育模式的结合体,马相伯依照中文“黎明”的意思,也给学院起了个贴切的西洋名字,法文是“奥罗尔”(L’Aurore),英文则是“奥罗拉”(Aurora)。
该校章程刊登在上海《翻译世界》期刊1902年12月号上。章程开宗明义公告学院旨在培养翻译人才。这似乎狭窄的目标实际上是马相伯现代化中国之愿景的基石。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那么依赖于获取西方知识,故此他相信最迫切的需要是培养能够将西方重要的书籍准确地翻译成中文的语言学家。自19世纪60年代新学之风兴起以来,翻译局非常时兴,但马相伯心目中的震旦学院决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局而已。对他,以及对少数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蔡元培和严复等人来说,翻译西方书籍比带进新技术和现代科学更有意义。因它们将向中国展开不同的世界观,新的理念,以及新的价值观。不过,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马相伯最为执著地相信,要使中国现代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势在必行。
马相伯倡导的现代化教育理念,比许多同代人放胆想像的更为深刻,更具改革性。此等教育理念在上海那些年轻的洋务派和革命者中间赢得了许多听众。马相伯常常论及他的教育理念,或许他早期的一位学生回忆他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其意:“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者,请归我。”
马相伯起初希望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开办大学,但1903年后,他的观念发生改变。他看到中国更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学院,这种学院如果不能领先于其他大学,至少应当与大学的发展同步,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其进深教育将专注于翻译西方书籍,以应实现中国现代化之所需,以及编订中国大学所需要的理科与文科的教科书。
此教育方法的核心有两个模式:一是可以追溯到唐代中国观念中的“书院”;一是法国观念中庄严的“学院”(académies)。马相伯在1886-1887年访问法国期间,就对这些学术团体特别感兴趣。“学院”不像大学那样被设定好的教程所束缚,它专注于更高的目标,鼓励求知欲,激发独立研究,并奖励学术研究。这些学术中心使他想起中国传统的学堂,中国学者在那里可以觅得奋发之境,从事研究和思想交流。这正是马相伯理想中的震旦的模式:一个既适合中国学术传统,又适合当前中国处境的西式院校。该校中文名字采用“学院”,既避免了时下外国人办学所乐于采用的“大学”一词,也避免了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旧时代的“书院”一词。
马相伯倾向于招收那些已经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并且在国学上已经得到认可的成熟的学生。选择主要是基于这些学生当具有的三个重要品质:
1. 掌握经典著作和精湛的语言技能,将有助于优雅、准确的翻译;
2. 博览中文书籍,熟知天下大事,将有助于选择中国最需要的西方著作,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3. 必须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应对密集课程和从事大量的独立研究。
震旦学院于1903年3月1日春节过后不久,就开始上课了,注册学生共有24名。开学典礼早在2月27日即已举行。激进派报纸《江苏日报》以“教育界的变革”为题,予以长篇报导。梁启超也针对这一重要事件撰文,登载于他的《新民丛报》上。他既赞扬了奠基人的学识,也褒扬了卓越的教育方案。马相伯在震旦开学前只是选择性地登过些广告,万没想到这么受人欢迎,但这并不阻碍他原有的目标(保持最高的学术水平)。一年后,在106名学生的名册上,有8名国家级学者和20名省级学者。
学院提供两年制课程,要求学生深入研习拉丁文,并且专修一门欧洲语言——法语、英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所有的语言课都强调阅读古典或现代西方文学名著。学生毕业的要求之一就是能将这些原著流利地翻译成中文。通过在教授指导下独立的学习,学生要在文学领域之外扩展他们的专长。他们有两种选择:选文科,要求学生专注翻译所有哲学分支学科的著作,同时也要学习翻译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法等领域的著作;选理科,学生则着重于学习翻译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著作。
尽管马相伯依赖耶稣会提供教学设备和师资,但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规定,在震旦学院,有关宗教教义的探讨不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虽然马相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直到晚年,他仍然乐于强调文科理科并重,连同其反对开设宗教课或传教的政策,构成了奥罗拉——震旦学院三项基本办学方针。
马相伯反映在教学法上的一个学术观念当归功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即主张学生应当学会独立思考。他认为,那些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应当屈从于类似多数大学和翻译中心里的那种密集强化班。上课不外乎介绍基本原理和规则,也就是被他称之为“理论”的每一学科的核心。一俟理论基础建立起来,马相伯就自视为导师,引导学生将理论应用在更为复杂的研究课题中,直到他们能够继续独立完成。
在震旦学院,马相伯总是展示出一种个人的、不拘礼节的教学风格。他的个人取向,和他的教学方法自然使师生关系亲密。学生们也很珍惜这样的关系。马相伯就像传统“书院”的师尊,学生是其年轻门生,聚其膝下向他求教。虽然课程不同,但均保留了那种传统的,在十分融洽的小组里向老师学习的方式。这种浓厚的“家庭精神”被看作是震旦的特色。
马相伯认为,震旦毕业生的特点应当具有概念性分析的技能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进一步激励学生,学校每星期天都安排一个集会,会上由一名学生按事先指定的题目——通常是时事——发表演说。然后与会者对演讲内容发表或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要以雄辩提出各自论点。这种公开的辩论会很受学生欢迎。
如此看来,震旦远非只是中、法两种教育制度的结合。马相伯在其中加进了其他的特色,使其更具独创性。震旦与洋务派和革命派皆有深厚之关系,这也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由于激进媒体的义务宣传,震旦收到了许多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的入学申请,他们都在寻求一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课程上,比大多数其他现有院校,都不那么僵化的学校。对马相伯来说,只要不妨碍学习进度,学生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都无关紧要。所以,他不担心招收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学者,而且他确信这些人日后在中国政治改革和现代化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他学生中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当属于右任。当时于右任因冒杀头危险出版了一本诗集,尖锐抨击政府而受到通缉。马相伯明知此事,但仍以化名招收了他。
除了每周讨论时事外,震旦学院的另外两个特征也使其颇似一所革命学校:一是每周三次军训;另一是学生积极参与行政管理工作。然而,这些特征并非马相伯刻意仿效其他院校,而是真实反映出他整个现代化救国的教育理念:
1. 辩论时事有助于学生将书本所学的东西应用于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
2. 进行军事训练,可使在校学生作好准备,将来要为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牺牲。
3.分担行政之责可教导学生自治,预备他们在更大的社会中,将同样的民主价值观应用在更重要的任务上。
如此,马相伯没有将学院的日常行政工作交给耶稣会的教师,而是委派给学生。每个学期,学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事以及由谁来负责。到1905年3月,最初的24位学生将所有的职务都轮做了一遍,只除了行政主管和会计二职仍由项微尘和郑子渔分别连任。这两位可说是震旦的共同创始人,因为他们协助马相伯一起创办学校,并一直是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在这种非同寻常、充满活力的氛围中,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引起某些耶稣会士的关注。这些耶稣会士是早期震旦的见证人,诚如他们回忆中所述:
(我们)记得这班学子彬彬有礼,勤奋好学,意气风发。他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年长的负责执行纪律。他们那时已经采用一些议会制方式,现在(1928年)这在中国学校中很流行。他们讨论、投票、贴出学校各项规定,但常常不遵守。
然而,其他一些耶稣会士对马相伯的办学方式与风格越发感到不安,甚至认为学校风气一团糟。1904年9月初,他们强加给马相伯一位新的副院长兼教务长——南从周神父(Father François Perrin)。此人对如何办好震旦持有相当不同的见解。他想建立一所纯粹的法国式“大学”,要求领导在上具有权威,有明确的学习课程,以及整齐一致、听话的学生群体。南从周责备马相伯缺乏强有力的权威,指责学生的自治组织干涉学校的办学方向,并分散学生的学习精力。他还认为学校课程设置太好高骛远。南从周强烈反对震旦学生参与反政府活动,怪罪马相伯将校园作为革命分子的避风港。他认为学校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害,弥补的方法为招收更年轻、更具可塑性,少有政治头脑的学生。
1905年春季学期,就在马相伯因病不在场的时候,南从周废除了学生自治组织,并削减课程。学生们曾试图寻找一个折衷的办法,但协商无门,最后只好投票表决,以130票对2票决定离开震旦。在医院病房中,马相伯流泪告诉学生:他没有背弃,也决不会背弃他们。为此他痛心地辞去了震旦学院院长的职位(日后校友称此学院为第一震旦)。于是他与学生们另觅新址,开办了一所新校,起名“复旦”,深含“光复震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