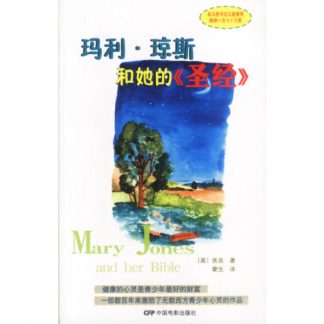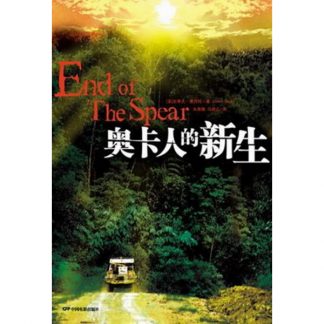描述
| 报佳音号 | 5620 |
|---|---|
| 外文书名 |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1665-1741 |
| 作者 | [美]魏若望(John W. Witek) |
| 译者 | 吴莉苇 |
| ISBN | 978-7-5347-2629-3 |
| 出版社 | 大象出版社 |
| 出版年月 | 2006.4 |
| 开本 | 32k |
| 页数 | 467 |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内容简介
本书以1699-1722年间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的生平为线索,介绍了耶稣会士中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为己任的索隐派的基本情况,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种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同时还通过傅圣泽返回欧洲后的活动,描绘了萌芽中的法国-欧洲汉学,以及与欧洲汉学和近代早期欧洲思想史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之争和18世纪欧洲中文图书的状况。
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深具思想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因被目为异端而长期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的文化史意义和比较文化学意义;礼仪之争中争议和权力之争的相互影响;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欧洲科学知识的动机和实践是否如李约瑟所评价的那样消极,等等。
本书英文本1982年首次出版,是一部较早专论索隐派问题的著作,其开创性价值至今不衰。作者为撰写本书广泛阅读傅圣泽的著作和书信——其中多数是未刊手稿,并将这些文献详细罗列,书读者开列出一份内容广泛、数量庞大、语种丰富的参考文献目录,使它还具备实用的工具书价值。
本书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同属这套丛书的有《耶稣会士张诚》、《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和《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等书。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作者简介
魏若望(John W.Witek,1933-2010),耶稣会士,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汉学、早期欧亚交通史和来华耶稣会士研究。著有《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南怀仁传: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Ferdinand Verbiest (1623–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利玛窦《葡汉字典》(Matteo Ricci’s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等书。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目录
总序
出版说明
中文版作者序
中文版序
致谢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区:开端,1687—1697
- 第三章 关于江西的一个传教士教区
- 第四章 在康熙皇帝的宫廷
- 第五章 重返欧洲
- 第六章 尾声
参考文献
- 手稿资料来源
- 手稿资料
- 西文资料
- 中文与日文资料
索引
译后记
附记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书摘
第四章 在康熙皇帝的宫廷
傅圣泽1711年接到的赴京上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耶稣会士同僚们通常都是因为其科技才能而被召进宫廷。 与此不同,傅圣泽被宣进宫则是因为他锲而不舍地想理解《易经》。 他是去担任白晋的助手,白晋对《易经》这部他称为最古老的中国经典的兴趣在1711 年之前就已持续几年,而且他也同皇上讨论过他的一些发现。 为了理解皇上下这道诏书的背景,首先需要勾画法国耶稣会士讨论某些中国经典的缘起。 那种讨论的一个产物就是索隐主义的萌芽,这是白晋、傅圣泽、郭中传和马若瑟支持的一种观点。 虽说他们即使在法国耶稣会士中也只占少数,但他们的作品非常丰富,无疑值得专门研究。本章要展现的是傅圣泽在索隐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索隐主义虽是少数派观点,但却成为在中国和在欧洲的西方人致力于以比较的眼光来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触媒。 傅圣泽在开始撰写其索隐主义论著的同时,也应召为皇帝执行一些特定任务。 而他作为中国传教区发展中重要事件的一名见证人在京九年期间(1711-1720),对本会同僚和其他传教士的不满情绪也日渐滋长。 无论如何这些冲突的结果深化了他对索隐主义的信念。
索隐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这四名法国耶稣会士想从中国经典中发现《旧约》人物的一种尝试。 如果不同时注意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区所面临的问题背景,这种描述会显得奇怪,甚至古怪。 1703年沙守信就中国人对天主教传教士所传播之福音的观点提出了一种认识。 他宣称中国人,即便是普通人,也对其他所有民族持有轻蔑之心,这是劝化他们的最大障碍之一;他又补充说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习俗和信仰如此着迷,以至无法说服自己承认中国以外的任何东西还值得他们注意。 当传教士向中国人指出他们祭祀偶像的行为奢侈浪费,或当中国人承认天主教是伟大、神圣又纯洁时,即使有人也许会下结论说这样的中国人准备归化了。 沙守信却坚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中国人会冷冷地回答说:“尔等宗教未见载于吾国之书;为外夷之教。 四夷之事及天下至理,焉有吾国博学鸿儒不知之理?”
每位汉学家都深知中国人这种排外情绪。 这不是清朝前期如此,因为利玛窦在晚明那些年里也同样经历过。 到此很应该回顾一下利玛窦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观点,因为索隐派们后来力争,他们的工作只是在发展利玛窦关于中国经典之思想的过程中对它的修正提炼。
利玛窦对道教和佛教是毫不含糊地一概否定。谈到理学时,则无论王阳明的观点还是朱熹的观点,他都不支持。 王阳明关于“理”的观点会导致唯心论,而唯心论无论从哪个角度也不能与担当天主教神学外援的经院哲学相协调。 朱熹尽管常常被与托玛斯·阿奎那相提并论,利玛窦仍然将其观点视为物质论而摈弃。他坚持认为宋代理学家误解了中国的经典著作,因此为了理解儒学必须追本溯源,也就是说要依据原始经典。 利玛窦之回归古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顾炎武的训诂考据运动———这一路向后来将发展为清代中期戴震和章学诚所拥护的“汉学学派”,这是一个需要更深入阐述的问题,尽管戴密微已宣称西方对清朝思想的影响是“间接的,不为人知的,其实是无意之举”。
利玛窦在思考中国哲学时,坚持儒学以“五经四书”为基础。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引用《中庸》的一些篇章时驳斥了朱熹对它们的解释。 反驳并非他那部名著的首要目的,其首要目的是阐明某些能通过自然理性加以证明和理解的法则。 他从“五经四书”中的大量篇章中找到了这些。 作为一部关于自然神学的论著,《天主实义》的焦点在诸如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全者、灵魂的不朽和上帝对人类善恶行为的赏罚这类题目上。②可见这篇论著是通向信仰的准备阶段,而非信仰的全部象征。
哪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曾力图指出天主教与中国经典所含法则之间的联系,沙守信1703 年仍在领教利玛窦将近一个世纪前就见证过的中国人的仇外态度,这也不足为怪。 一般而言,利玛窦以后的耶稣会士仍遵循他的观点,越过理学家而回归古代经典中的纯粹儒学。然而许多耶稣会士却排斥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因为他们相信该书通篇迷信,无论是《易经》本身还是对它的各种注释都不包含精深教义。 对《易经》的这种观点至少是白晋对其诸会友之解释的看法,正如他担任康熙皇帝特使出使路易十四宫廷期间在法国写的一封信所表明的。白晋的信以反驳阎当 1693 年训令为主,分为三个主题:(1)对耶稣会士使用“天”和“上帝”之术语的辩护以及禁止继续使用该术语将在法国引起的相应后果;(2)关于耶稣会士教堂所悬“敬天”匾额的报告;(3)为遭阎当训令攻击的卫匡国、利玛窦和康熙皇帝辩护。依白晋之言,阎当在训令的第六部分谴责了一些被认为是错误、轻率和遭人非议的命题。 白晋发现其中三个命题比较重要:(1)如果理解正确,则中国人信奉的哲学中没有任何内容与基督宗教律法相违背;(2)“太极”即上帝,为万物之源;(3)《易经》是中国人最上乘的道德与自然哲学教旨之浓缩。白晋声言大多数耶稣会士都不会赞同第三个命题,但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特定的渠道来获知中国哲学的正当原则,而中国哲学若能正确理解至少会显得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有道理。 在白晋看来,三个命题都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上,他相信他可以通过“分析被君主制的创立者兼中国首位哲学家伏羲附入其法则的《易经》中的神秘人物”而证明第三个命题为真。白晋补充说让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皈依天主教,再没有比向他们展示天主教如何符合他们祖先的法则与他们的主导哲学更合适的方法。 他同意中国人的当代哲学不适于达成他的目的。 因此他正在重写许多早已准备好的关于这题目的报告。 他希望这些报告的良好效果将足以替代他亲赴罗马所能达成的成果。
离开巴黎返回中国之后,白晋依然保持努力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 虽然铎罗使团来华之前,白晋对《易经》持有这种观点大约已有十年,但他还没有非常成功地创建一个由三四名耶稣会士组成的“学派”来帮助他发展他所宣称的在经典中的发现。 这多少是因为他必须要等几年以待他从法国带来的第二批耶稣会士具备阅读中文的能力。 三位索隐派(马若瑟、傅圣泽和郭中传)中最早在书信里谈到索隐主义的是 1704年马若瑟写给白晋的一封信。 在表达了收到白晋讨论有关中国象形文字之发现的4月29日来信的喜悦之情后,马若瑟说久未复信是因为他不仅读了伏羲的六十四卦,也读了文王和周公的注解。 他自己的任何评论都只是初学者的皮毛之见。马若瑟提醒白晋他们两人都与普遍流行的意见相左,不认为伏羲是中国字的创造者,而认识到现在的中国文字并非古时文字。 古代学者并没有在木简和竹简上刻字的艺术,因为他们只能粗糙地画出表示一项事物例如龟的整个外形。 合成字的字义通常可以从构成字的两三个偏旁部首中获知,例如“怒”或“活”。 《说文》和《释名》都有对这些字的解释。 然而马若瑟认为应当研究的不是合成字而是独体字。 他希望在自己关于《易经》的作品中开展这项工作,这作品不会是一部完整的论著而将是一系列书信。以上是对铎罗使团来华之前索隐派运动的一个简单回顾。